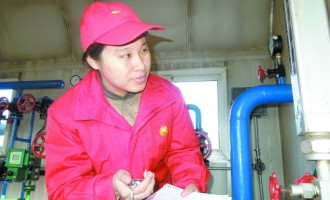和劉金光約了幾次,他終于答應放下手頭的工作,要和我好好談談了。
剛剛下站檢查回來,他草草地用過晚飯,坐在采氣管理六區公寓院子的小亭子里,夕陽的余暉將這里映照得暖意盎然,劉金光的思緒被時光拉回到10年前。
2003年5月,當大牛地氣田先導性開發試驗時,劉金光從新疆工區被緊急調到大牛地,“那時候,正是‘非典’鬧得正兇的時候,一路上算是沖破重重關卡吧!”從川西培訓回來后,參加到了1號集氣站的建設當中。
困難當頭唱響開發前奏曲
“生產上的、生活上的,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做,車輛壞了,都只能自己動手維修”。劉金光回憶起當年的工作狀況,有點唏噓感慨,“很困難。”
當年的困難,絕不是現在他的一句“很困難”就能概括的。
為了氣井能盡早投產,幾口單井的井場上,安置的真空加熱爐需要加足軟化水,“單井道路全是用推土機推出的一條小路,再墊些沙柳條子,車子很難開進去,就雇傭老鄉家的毛驢車往里拉水,大家也都是手提肩扛的,DK10、D11、D13幾口單井的加熱爐全加滿,用了70多個小時,一直沒合眼,大家都攢著一口氣,盼著開井生產的那一天。”
2003年9月2日,時任采輸隊副隊長張亞軍,打開了大牛地氣田第一口開發井鄂9井的閘門,對管網進行置換;時任集團公司副總裁牟書令下達了點火命令,大牛地氣田正式供氣。“火焰不僅映紅了我們的笑臉,更是把我們的心也燃燒了。”
“沒有越冬生產經驗,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。”站場的水井被凍堵了,“連做飯都沒有水,從老鄉家借了幾個陶罐,用驢車來回拉水,整個站場的水暖設施全凍壞了。”趁著那幾天暖和一些,劉金光和同事們趕緊開始改造整條采暖管線,給水井裸出地面部分穿上厚厚的用石棉做成的“棉衣”。一年后,劉金光調到3號站時,再次遇到這個問題。他雇傭當地老鄉,用原始但卻很有效的土式打井法,在綜合房內打了一口水井,解決了冬天用水的問題。劉金光把這一做法向隊里做了匯報,這為以后新建集氣站的水井位置,做好了規范標準。
“那時,我們每個人都是采氣工、巡檢工、維修工,一人都是身兼數職。”站上有一部使用了多年的老爺車——北京213,“就是這樣的車,每天24小時都閑不著,巡井、預防解堵、給守單井的員工送菜送糧。”有一次,這輛老爺車終于趴了窩,劉金光只好乘便車下榆林城,滿大街找配件,“回來自己維修,打著手電筒,連夜修,要不啥事都耽誤了。”大牛地隆冬深夜,氣溫下降到零下30多度,為了能順利地把車修好,劉金光和他的同事們硬是沒有戴上手套,“冷的不行,戴著手套也不管用,一會就凍透了。”當車子的發動機終于發著了時,“心里啊,別提有多興奮!”但整個身體都快僵硬了,大家都想喝口熱水暖暖身子,“那手怎么都端不起水杯,直抖!”
下馬威也難不倒我們采氣人
進入冬季的大牛地,給了這群來自中原的漢子們下馬威,工作更困難的是給單井做預防。1號集氣站所管理的第一批投產的開發井,采用低壓進站的采氣工藝,井場上的流程比較復雜,從采氣樹、真空加熱爐到高架緩沖罐,每口井就是一個小小的“集氣站”。“現在給單井做預防,打開注醇泵就能做,那時沒有化排車,做預防都是人工往井內灌乙二醇。”他們在套管閘門上連接上兩節油管,高高翹起,灌上乙二醇后,關閉和打開相應的閘門,利用落差,藥液就自流進井底。他們開上那輛老爺車,拉上幾桶乙二醇,來回奔波在幾口井之間,“每天重復著同樣的工作,那時也沒有覺得煩。”下過雪的大牛地格外有魅力,但這種“魅力”在劉金光們的眼里可就變成了“沒力”了,“下過雪后,車子都進不了井場,要想到井場只能步行,背上桶藥劑,有的單井來回就是4、5公里。”
每天要巡井兩回,最早的一次要求在8點以前要把巡井數據報回站內。“冬天只能5點多就起床,首先要伺候好那輛老爺車,沒有車庫存放,車一停下,就打不著火了,給油路預熱,是個麻煩事,每天都要鼓搗近一個鐘頭,才能上路。”往D10井去的路上有一條小河溝,沒有橋,“天不冷的時候,可以脫了鞋趟過去,天冷了,倒是可以開車過去。”劉金光回憶此事時,還念念不忘,“不知道現在怎么樣了。”
“我們1號站比2號站強多了,他們是采用高壓進站工藝,采氣管線老堵。”由于采用低壓進站的采氣工藝,天然氣在井場就加熱分離處理了,1號集氣站的單井采氣管線沒有堵塞過,“但是井堵很頻繁,有時剛把這口解完,那口又堵了。”他們的解堵方法很原始,全是用人工往井內油管灌乙二醇,“灌進去了,憋上十幾分鐘,打開放空閥門,水合物噴出來后,有時呈棒狀,最長的有半米多長,很危險。”單井剛投產沒有多久,壓力都很高,放空時,氣柱直沖云霄,聲音震耳欲聾,真的可以用地動山搖來形容了。“那時都沒有見過耳塞是啥樣,我們都是用衛生紙把耳朵塞住。”
勞動強度隨著大牛地氣田的第一輛化排車的到來,有所減輕。“那時主要是給2號站站配備的,他們是堵井的‘重災區’啊!我們有時剛從2號站借過來,他們就打電話過來催,等用完去還時,他們連我一塊扣下了。”看著我詫異的表情,劉金光笑笑解釋說,“人少,幫他們上井解堵去了,忙完這頭,忙那頭,雖然很累,但那時的狀態出奇的好,沒有一個人叫苦喊累的。”車里每天都拉著行車必備的“寶貝”——幾把鐵鍬和幾根木棒。“沒有四驅的車,在毛烏素沙漠里行駛,不帶上這些,有時真是寸步難行。”車輛於在沙子里,最好的辦法就是墊木棒,用鐵鍬挖,“每個人都練成了一身好功夫,一會就把車子從沙子來開出來,但不知道能走多久,又就被於住了。”
痛并精彩的采氣生活
2004年 10月22號,3號集氣站建成投產,劉金光隨即調往該站。
3號站地處陜蒙交界地,“往南一步是陜西,往北一步到內蒙”,所管理的氣井屬于DK13高產井區,僅DK13井日配產就高達7萬方。“當時采輸隊僅有1、2、3、5號集氣站,其中3號站的采輸量是最大的,占了半壁江山,我們站堵一口井,管網壓力馬上就下降。”
那時的集氣站還沒有配置對講機,“通訊基本靠吼”,調配產時,都是一個人在站場上控制節流閥,另一人在自控室內監控,每調整一下,都要及時跑到窗口吼,“下調100”,“上調50”,每天都有這個節目上演,“我們開玩笑,鍛煉幾年后,我們都可以和帕瓦羅蒂同臺演唱了。”每小時必須記錄的關鍵點壓力和溫度,也是拿著草稿本到站場上一一巡查記錄好,回到自控室,再認認真真地抄寫到班報表上。
這樣的工作狀態給每天單調的生活,增添了幾絲樂趣,最讓大家難以忍受的是晚上睡覺時,宿舍隔壁那臺發電機發出的噪音。“地方電網的大電接不上,只能自己發電, 24小時不停機,晚上躺在床上,渾身的肉都直跟著顫抖,癢癢得難受。”
再怎么無法忍受發電機帶來的麻煩,卻也離不開它,只要有一點故障,整個站場的工作幾近癱瘓。任勞任怨的發電機發了脾氣,水箱漏水了,“想罷工,那可不行。”發現水箱漏水已經是晚上9點多的時間,維修水箱需要極高的焊補手藝,也只能白天趕往榆林城找高手修補。可是,在到天亮這么長的時間怎么辦?發電機不工作,注醇泵就運行不了,氣井堵塞的幾率就會大大增加,配產任務也就完成不了,這可是占了半壁江山的產氣量啊!
最有效的方法是給發電機的水箱,不斷地加水,來保證循環降溫。
“大家都把自己的臉盆端出來,放在水箱的下面,接住漏出來的水,再往水箱里添入。”李洪峰在發電機旁值守了整整一夜,不斷地重復著這個動作,“耳朵都快被整聾了”,這一夜過后,“走到哪,耳邊都是發電機轟隆隆的聲音”。
當第二天傍晚,劉金光提著焊補好的水箱回到3號站時,已經近10小時沒有注醇的氣井也鬧開了脾氣,“配產最高的DK13井堵了,外輸流量急劇下降,2號站那邊已經打來好幾次電話。沒辦法,只能裝好水箱,先讓發電機運行起來,能注醇了,解堵也就好辦多了。”劉金光顧不上“咕咕”叫的肚子,“連口熱水都來不及喝”,急忙召集大家一起把水箱安裝上。
劉金光從DK13井上解堵回來后,已經接近午夜時分,連續十幾個小時的忙碌,讓他感到極度的疲憊,“上下眼皮直打架,當看到站場上燈火通明時,心中有一份說不出的自豪感。”
(華北石油 高宗全)